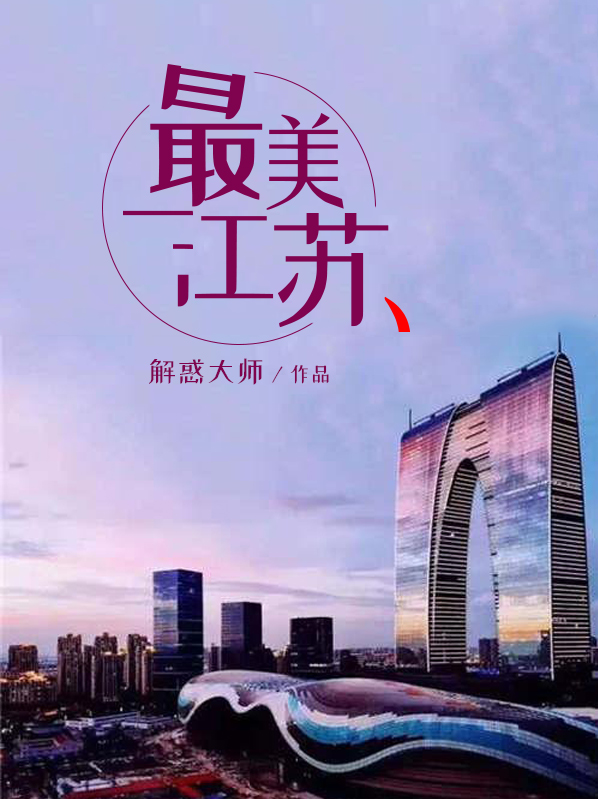“夹这么紧做什么?慌了?”
盛瑰听着耳边那裹着欲念的低哑声音,下意识往后缩了缩。
耳上传来一阵刺痛,伴着热气喷上来的酥麻痒意。
祁修谨咬着她瓷白的耳垂,箍在她腰上的手重了几分:“放松,不然我不确定要折腾你到什么时候。”
外面始终有脚步声来来往往,仆人们正在迎送宾客,没人想得到书房里会是这么荒唐的一幕。
今天是祁家老爷子八十大寿,祁家小辈们都来了老宅,海城的名流更是都来道贺。
听着门外那些客人来往的动静,她克制着战栗压着嗓子求他:“别在这里行么?要是被看见……”
“看见就看见,怕什么呢?”
男人喉间溢出一丝低笑,漫不经心磨着她:“当初你勾我的时候,胆子不是很大么?”
盛瑰咬着嘴唇,口腔一片浓郁的血腥味,心也一点点冷下来,压着哭腔开口:“饶了我好不好,外面有那么多人,如果被发现,祁家的名声怎么办?”
祁修谨扯了扯唇,俯身衔住她耳垂不轻不重咬着:“我在这里,他们敢说什么?”
盛瑰的心彻底沉了下来。
祁修谨是不用怕什么,他是祁老爷子最看重的长孙,是祁家现在的掌权人,不用像她那样伏低做小。
他们不敢对祁修谨说什么,可她母亲只是已故的祁家五爷的二婚妻子,她这个拖油瓶,就更加惹人嫌。
如果被发现跟自己的堂兄在书房偷情,等待她的下场会是什么?
别人一定会觉得她不知检点,在老宅就敢勾引自己名义上的堂哥,哪怕知道是祁修谨主动提的要包养她,也会把罪名都安在她头上。
她和母亲会背着恶名被赶出海城再无容身之所,但他一点不在意。
反正之于他,她不过是个玩意儿而已。
从三年前被他包养时就该知道的事情,她却到这一刻才能彻底确定。
盛瑰指尖几乎断裂在掌心,忍着疼迎合他,只想快些结束。
偏偏祁修谨瞧出了她的心思,舌尖绕着她脖颈敏感处撩拨,掐在她腰上的手轻拢慢捻摩挲着那细嫩的软肉,动作也带了些逗弄。
盛瑰的神经更加紧绷,死死攥着身下碎裂的礼服裙,强忍着不肯出声。
于是祁修谨的动作更加放肆。
她身下的裙摆眼下已经被攥得皱巴巴,还带着暧昧的湿痕。
盛瑰终究受不住,放软了声音求他:“你快点……”
祁修谨掀了掀唇角,猛地抵紧深处:“嗯?你就是这么求饶的?”
难耐的娇吟从盛瑰口中哼出,她紧咬着舌尖才算按捺下来,伏在他肩上低低叫了声哥哥。
祁修谨这才满意,加快动作粗喘着结束。
盛瑰早已没了力气,后背被办公桌硌得酸痛,勉强从桌上坐起来,差点腿一软摔在地上。
祁修谨扶了她一把,扣好扣子整理了领带,又变成了矜贵清冷的祁家大少。
而她狼狈不堪的模样映在漆黑的电视屏幕上,满身红痕,衣衫凌乱,眼角还有几分泪痕。
祁修谨让心腹特助送了套衣服来,看她垂着眸子不说话,攥着她手腕把她搂到怀里:“这就生气了?真不经逗。”
盛瑰不软不硬开口,声音还带着哑:“不敢生大少的气。”
祁修谨拧了拧眉,大概是看她被折腾得实在有点可怜,难得有耐心:“过几天带你出国玩一圈?刚好巴黎有个珠宝展,有一对蓝钻耳环应该很衬你。”
盛瑰别过头,语气听着淡淡的,却带着些不易察觉的自嘲:“不用了大少,我没有耳洞。”
跟了他三年,他那么喜欢咬着她耳垂厮磨缠绵,居然连这个也没注意到。
听见她一口一个大少,祁修谨终于没了哄人的心。
那微凉的手掐住了盛瑰下颌,逼着她跟他对视:“你在跟我闹脾气?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?”
盛瑰看着那双染着薄怒的墨眸,明知故问:“您是说情人的身份,还是堂妹的身份?”
祁修谨手上加重了力道,当真怒了:“盛瑰,你真要惹恼我?”
他从小就是祁家众星捧月的长孙,大概从没有人敢这样顶撞他,眼下动了气,周身压迫感更甚。
盛瑰垂眸忍着疼,也隐忍着自己眼底那一丝挣扎,声音有点嘶哑:“老爷子刚刚说苏小姐快回来了,也在催大少早些将婚事定下来,我再巴着您不放,就有些太不识趣了。”
祁修谨听见她这么说,目光死死锁在她脸上,忽然冷笑出声。
“不错,长出息了,盛瑰,你别后悔。”
那声音幽冷凌厉,仿佛房间里的气温都低了好几度。
扔下这句话,他松开手,像是甩掉什么垃圾般面无表情擦了擦指尖,绷着唇拿起自己的西装离开。
没过太久,书房的门便被敲响。
盛瑰将门打开,女助理走进来将纸袋递给她,眼神有点意味深长:“您先把药吃了吧。”
盛瑰貌似平静的接过,手指却细微的发着颤,道了声谢拆开药送进嘴里。
书房饮水机空了,她直接干咽了下去,呛得眼圈通红。
倒也不是不能出去倒了水再吃,但助理进来本就是要盯着她吃药。
祁修谨再放肆,也不会让她怀上他的孩子。
早点把人打发走就行了。
助理也没管,放下衣服走了出去。
那件衣服是某个高奢品牌刚出的新款,一群千金小姐抢破了头,在祁修谨这,就只是随便给她的玩意。
平心而论,他是个极好的金主,哪怕她只是苏韵颜的替身,他对她也算很纵容疼护了。
但替身总比不过正主,刚刚寿宴上老爷子刚提到苏韵颜要回来,他常年冷寂的眼都化了冰。
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,她看祁修谨就是这样的眼神,做不得假。
盛瑰换好衣服走出书房,却在楼梯拐角遇到面色有些慌张的母亲盛淑敏。
“你这丫头去哪了?宴会结束就不见了人!”
母亲的手按在她肩膀上,刚刚被祁修谨咬过的齿印又泛起了疼,丝丝缕缕渗入骨髓,又莫名其妙漫到胸腔。
盛瑰咳了一声压住嗓子里的哽咽:“我刚刚不小心把衣服弄脏了,让同事给我送了一套过来换。”
盛淑敏打量着她身上崭新的衣服,没察觉什么异样,似乎松了口气,语气带着责备:“麻烦人家做什么?宴会都散了,弄脏了就回房间好好呆着,万一惹出麻烦呢?”
顿了顿,她又道:“刚刚那位大少不知是被谁招惹了,下楼的时候脸色难看得像是要把宅子掀了,我找你的时候听仆人说好像看见你跟他一起,可把我吓坏了。”
“你可千万不能招惹那位,更不能有什么心思,知道吗?哪怕在一个屋檐下,大少跟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”
“我怎么配跟他有关系?”
盛瑰勉强扯了扯唇角:“就是下楼的时候刚好遇上,大少根本没正眼看我。”
盛淑敏这才放心,撇开她下楼。
盛瑰看着母亲谨小慎微的模样,有些怔松。
她母亲是个身世不明的孤儿,父亲在她没出生时就去世了。
母亲艰难拉扯她长大,能带着她二婚嫁进祁家,已经是了不得的高嫁,可继父却在一年前去世。
至此,她在祁家越发伏低做小,对仆人都是一副讨好的笑脸。
要是她知道,三年前她意外跟祁修谨发生了关系,还被他包养,她大概会吓死吧。

100书币

388书币

588书币

888书币